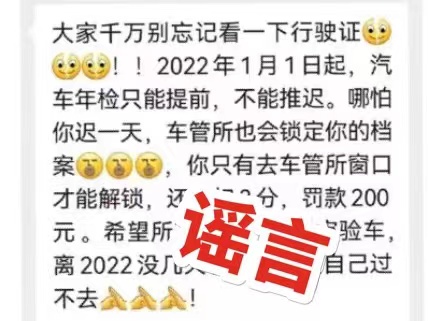日前,山东大学彭实戈金融数学创新团队实现中国数学会华罗庚奖、陈省身奖、钟家庆奖“大满贯”,成为继复旦大学偏微分方程团队之后,全国第二支包揽三大奖的团队——
□ 本报记者 刘一颖 杨帆
日前,在中国数学会2022年学术年会上,来自山东大学数学学院的90后副研究员杜凯被授予第十六届钟家庆数学奖,以奖励其在平均场正倒向随机博弈与控制方面作出的贡献。这是山东学者首次获得这一殊荣,标志着山东大学彭实戈金融数学创新团队实现了中国数学会华罗庚奖、陈省身奖、钟家庆奖“大满贯”。
 (资料图)
(资料图)
中国科学院院士、山东大学教授彭实戈提出了倒向随机微分方程理论,并将原创性“非线性费曼-卡茨公式”应用在金融领域,被誉为“中国金融数学第一人”,于2011年摘得第十届华罗庚数学奖桂冠。山东大学副校长兼数学学院院长吴臻在随机递归系统的最优控制理论和方法研究上取得一系列创新性、突破性成果,提出的嵌入方法为金融市场实现最优投资提供了一种基础理论工具,于2019年获第十七届陈省身数学奖。
值得注意的是,吴臻是彭实戈的首位博士生,杜凯师从吴臻攻读博士学位,这意味着山东大学数学学科建成完善成熟的人才培养体系,具备了自主培养一流人才的能力。“三代人”接续奋斗,聚力原创突破,在数学领域基础研究自由探索,始终走在学术研究前沿。近日,我们来到山东大学,采访了三位获奖者。通过他们的自述,我们可以看到高深莫测的数学研究背后科学家的日常。
彭实戈:专走没有的路
我特别喜欢数学。下乡期间,每晚油灯陪我学习到深夜。有一天夜里,我解题遇到难关,想起在45公里外的一个村子里也有位喜欢数学的人,叫王志圣,就决定去找他。那时候没有交通工具,只能靠走,我走了一个通宵,清晨见到了他,和他讨论了一天,回来时,又走了一个通宵。
我进入山大工作也是曲折的。起初,我在山大物理系读书,毕业后被分到广播站任技术员,又调到无线电厂当供销员。但我一直研究数学,反复修改的论文《双曲复变函数》几经辗转,到了山大数学研究所所长张学铭教授手中。是他,将我调到了山大数学研究所。
1983年,在组织推荐下,我到法国学习交流。除了完成导师布置的课题,我还给自己出了不少难题。我当时提出了“含高频振动的最优控制系统均匀化理论”,为证明这个理论的科学性,准备博士论文时,我把这个发现放在第三个章节。
出席博士论文答辩的评委都是有名的数学家,如果不把握住这次答辩的机会,怎么能和专家们讨论我研究的问题呢?论文读完了,专家们很认可。我发现,一流的数学家欣赏的正是开创性的学术思想,这极大地激发了我进行原创性研究的兴趣。
可能大家认识我是因为倒向随机微分方程,这也是我的学术成果之一。什么是倒向随机微分方程?假使我们为将来设定了某个目标,根据现在的能力、财力能否达到?如何达到?解决这问题的关键,实际上不是从现在向未来分析,而是由将来向现在推导,这就是倒向随机分析。而通过策略的制定逐步把不确定性抵消,把风险规避,就是倒向随机微分方程所要解决和计算的问题。围绕这个主题,我在概率论、随机控制理论和金融数学领域获得一些研究成果。
提起这项成果,还有个小故事。当时在进行这项研究的时候,我和合作者Pardoux想了很久也没有进展。有一次,我俩一起在上海游览豫园。晚上回到宿舍,我还在使劲想,忽然灵感一现,找到了突破点。我抓紧演算、验证,真算出了结果。我也不管几点了,就给Pardoux打电话。他说,你知道现在几点吗?我说,我找到了。
金融数学是大家很关注的一门学科,确定在这个方向研究,也是“阴差阳错”。我当时有个发现,就是“非线性费曼-卡茨公式”,一直认为它应该应用在物理学领域。我带着这项研究成果,遇到国际知名金融数学家El Karoui教授,她认为,这个成果应该应用在金融学领域。我有点失落,我以前认为金融就是会计,怎么还需要数学?
但我还是开始系统研究金融方面的资料。果真,有了突破。那时候期权期货交易很热,我从数学角度出发,发现交易中存在严重问题,盲目投资会造成我国资金大量流失。于是,我给学校和地方写了信,汇报了这一发现。有说法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若不及时叫停交易,会流失千亿元国有资产。
除了研究数学,我还很喜欢爬山。我爬山不走大路,专走小路;不走已有的路,专走没有的路。
吴臻:不是“为了去证明哥德巴赫猜想”
山东大学数学学科诞生于1930年,近百年的历史积淀也体现在我们人才培养方面。这次获奖,充分说明我们团队具备了培养新一代优秀数学人才的能力。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能够取得相对丰硕的成果,首先得益于有高水平的大师。大师带出一支高素质的队伍,从而取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走在了国际前沿。
导师十分重要。如果没有一位高水平、高层次的导师,学生想“自我成才”非常难。我们与华罗庚等大师所处的时代不一样,他们大多靠自己探索。如今,没有一位好导师,就很难找到处于国际前沿的研究方向。有可能你所选择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问题,别人已经涉猎并取得了重要进展。
所以,为人师者,要有很好的学识、较高的学术水平、超前的视野,具有发现问题、指出问题的视角和眼光。这才能保证所带的学生通过自身努力,很快走在学术前沿。如果导师研究的方向是“夕阳”,没太有价值,学生再努力也很难有重大突破。
如何才能一直走在学术前沿?导师要不断去挖、去找寻新的“矿”,找新的研究方向,也要培养学生具备这种思维,不能因为年纪大就不寻找了。像彭老师70多岁了,但在学术上,心态始终保持年轻。他不断往前走、去探索,这是导师的自我要求。导师如果固步自封,觉得进行的这些(研究)差不多了,指望学生再去自由探索,这是很难的。
还有一点,导师要教给学生认真仔细、严守规范。学术研究,没有小事情。不要觉得打个字、写个报告,出现点笔误,很正常。在指导学生时,导师要帮助他们养成规范严谨的科学态度,这很重要。有的学生这个无所谓,那个不在意,由一点点不严谨慢慢发展成做什么都粗枝大叶。常常觉得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实际上,步骤中有一堆问题。
数学是严谨的学科,处处是漏洞,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有的导师在这方面可能抓得不够严,反正看上去是对的,但数学是“细节决定成败”。因为数学的证明、定理,细节不对,整个都不行。数学也靠感觉,但不是“你感觉行,就行”。
所以,导师不仅要以身作则,还要严格要求,不能轻易把“学生的偷懒”放过去。得从根上引导他们建立好的学习习惯、工作习惯,培养他们细致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从而一点点扎实地进步,这一点非常重要。
和应用学科基础研究坚持“目标导向”不太一样,进行数学研究,更多的是自由探索,不一定就是“为了去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冲着既定目标直接开展研究,反而会非常盲目。
不同于物理、化学这些学科,数学更加基础。想要认识数学、理解数学,不仅是学习一些数学的技巧,首先要有一种研究的心境,能够踏实地坐“冷板凳”,有“几十年磨一剑”的心态。
进行数学领域基础研究,是博观约取、厚积薄发。首先要静下来,相对自由地在数学的天空中探索一些哲理性、原理性的问题。经过漫长的思索,逐渐去凝练数学的理论,形成原理性的共识,逐渐提炼出数学结果。数学研究,往往会解决一个特别远大的问题,它中间的步骤不是这么明确。如果非常明确了,坦率地讲,数学的价值就没有这么大了。很多时候,解决数学领域的远大问题,是在探索之中慢慢找到道路的。
没有雄厚的数学知识基础,想成为一位数学家,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清醒认识,即使目标方向未必十分明确,也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数学书籍都比较难,很深奥。有可能看了这些书,也没有什么收获。因为这些书都是前人的创造,即使看懂了,也是把前人的成果看懂了,并不是自己的成果。
你的目标在哪里?这就是一个自由探索的漫长过程。就像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到的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进行数学研究感到非常迷茫,非常遥远,走到哪儿,也不知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长时间辛苦探索,有可能过了一段时间,能看到灯火阑珊,收获一点成功的喜悦。“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看到灯火阑珊也不是抵达光明的顶点,只是阑珊,也就是说,你可能进行一段研究会得到一点收获,这鼓励你不断地去研究。
开展数学研究需要远大的理想和信念来支撑,否则可能走不下来;如果得到一点小的成果就沾沾自喜了,这也不行。没有远大理想,成不了数学家。所以,数学研究的“目标导向”指的是理想信念,坚持不懈。用远大理想支撑信念,让自己不折不挠地登攀,不断前进。
有一位杰出的导师,可以让你站在更高的山上去攀登,站得高、看得远,比同侪更具研究的优势。但如何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是我留校当老师后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记得很清楚,刚博士毕业的时候,和彭老师聊天。我说,博士毕业了,我现在是老师了,可以顺着彭老师开拓的领域,继续往下进行,但相对而言自由探索成分少一点,当然这个领域也有很多问题值得去研究,但是这些问题可以由彭老师当时指导的博士生去研究。如果只是延续,相对而言挑战性就不够了,也不利于自己不断地再去努力、去进步,还有一个问题是,怎么带自己的学生,我的学生进行哪些研究。
彭老师说,没有什么捷径,就是博览群书,看论文的范围更广阔一点,看之前不太熟悉领域的论文。听听学术报告,听你不太熟悉的数学家的报告。还有就是要静静思考。
经过长期漫看、漫听、漫思,实际上就是自由探索,慢慢地能够发现一点新的问题。所以,我在彭老师原来不太研究的方向里研究了一些东西,比如部分信息下随机系统的最优控制问题。
自由探索说起来容易,但它需要一个相对平稳、不浮躁的环境。这就与国家发展、社会环境紧密相关。国家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肯定与国家发展的步伐一致。当国力不够强的时候,面临外来挑战时,肯定要先去制造飞机大炮。当国力足够强大时,就有环境去进行长周期的基础研究。只有国家强大了,才能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基础研究人才。
我是70后,当时有许多同学都选择出国,觉得国外条件十分优越。我读研究生的时候,电子资料很少。为了看一篇纸质论文,得去国家图书馆或者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的图书馆查阅。首先得开介绍信,到图书馆找论文,找到后,再借阅复印出来,成本很高。1998年,我出国读博士后,第一次到法国,去大学图书馆一看,发现想看的杂志都有,查阅很方便。
当时我从济南去法国,得先坐火车到北京。我现在还很清楚地记得坐的是2598次列车。晚上坐火车,早上到北京。从北京火车站坐大巴或者打出租车到机场,坐飞机到法国。在法国,巴黎与勒芒相距200多公里,高铁只需50多分钟,能很直观、真切地感受到国家的发展差距。
但现在不一样了。国家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和投入,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国内教授的收入和法国教授的差不多,甚至比他们的待遇还要好。科研经费的投入也提高了很多,我们可以出去访问、交流,想看的专业电子期刊在学校图书馆都能查到。
基础研究人员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大家享受的医疗、子女的教育情况也越来越好。这让我们进行研究有了相对安稳的生活环境,能够心无旁骛地去探索。
现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年轻人受到网络等影响,特别希望“短平快”。更容易获取信息当然是好事,可以节省时间,但进行基础研究想很快成才,也难,因为基础研究的“基础”很大。看数学的书不可能一目十行,得慢慢看,这需要很多的时间。而且随着学科的发展,越积累越多,不把它搞明白了,不太可能有所突破。
不是鼓励所有的人都去进行基础研究,因为也有许多问题需要工程技术来攻克。基础研究是有门槛的。除了天赋、勤奋、保持心态,还要有灵感。勤奋可以做到优秀,但是要到杰出,还需要一点灵感,需要一点天赋,需要与生俱来的数学思维能力,这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许多数学大家能实现原创性重大突破,他们的共性就是能在别人“熟视无睹”中,发现解决问题的技巧。这就需要机遇和灵感。
杜凯:只要足够感兴趣,那满眼都是它的好
我的本科、硕博都是在山大读的。在本科高年级阶段,听了很多专家学者的讲座。其中记忆最深刻的,是彭老师给我们讲金融数学的期权定价问题,是用倒向随机微分方程解释的。那时候,金融很热门、很常见,但没想到,它背后还蕴含着这么深刻的数学逻辑。
硕博期间,吴老师问我的第一个问题也是关于金融应用——可转换债券背后相关的原理。通过研究倒向随机微分方程,就可以解释债券所具有的一些性质,这让我觉得非常神奇。通过定量的分析,能解释摸不着、看不见的问题,非常有意思。
以几个简单的金融问题为切入点,慢慢聚焦其背后的数学问题进一步研究,再到发现这些数学问题又能引申出更多的知识和内容,我渐渐感受到数学的魅力。
当然,进入一个新的领域,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作为门外汉,只能看到表面,不知道其内层、深层的逻辑和含义。这时候,导师非常重要,他会指给你一条明确的路,告诉你看似复杂的东西其本质是什么。在老师的引导下,就像提前开了天眼,知道如何进行研究,知道从哪个方面切入更合适。
透过表面看事物内层的深刻含义,也是数学教给我最有价值的东西,这让我能够更加清晰明了地认识事物,更加准确地理解现象。
这的确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像有些人说坐“冷板凳”。但在我看来,如果找到了很热衷、很感兴趣的领域,就不会有坐“冷板凳”的苦闷。只要足够感兴趣,那满眼都是它的好。
进行基础研究,离不开兴趣。求知欲是推动我们进步的关键点,一直保持对知识探索的欲望,一直有新鲜的事物在引领,人才能不断向前走。起初,探索欲望没那么强烈,因为像数学这类基础研究,难就难在发现问题的过程。这时候就需要导师的指点和团队的帮助。
就我个人而言,我读博士期间以及博士刚毕业时,基本是依靠团队各位老师的帮助才一步步认识到如何去进行研究。还有一点,从彭老师到吴老师为团队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如果没有前辈解决了这些关键性的难题,就没有我们后来者进一步拓展。
就像人们常说的,踏上一条路,你不需要知道这条路好不好走,只需要知道这条路对不对。只有路对了,走下去才有意义,即使它再坎坷再布满荆棘。而如果我们不知道这条路对不对,就往下走,很有可能就是走向了一条死胡同。
所以我认为,前辈们摸索出来的这条正确的道路非常重要,而我们只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努力尝试着往外多走了两步。
基础学科研究,就像牛顿所说,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一步往外看。我现在也开始给更年轻的学生讲课,也会涉及基础研究的内容。我在给他们讲理论的时候,会尽可能地举一些实际的例子,让他们可知可感、更好理解,也让他们对这方面的研究更感兴趣。就像我前面所说,只有对一个领域感兴趣,才能支撑着人继续研究下去。
我希望能帮助我的学生们在本科阶段少走一些我走过的弯路,让他们更早地认识到自己适不适合从事研究,想不想从事研究,努力把我积累的经验分享给他们。
数学,就是一个聚宝盆。一层一层地拨开总能发现惊喜,永远有新的东西等待着去探索。越往后研究,就越能发现它蕴含着深刻的逻辑之美。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