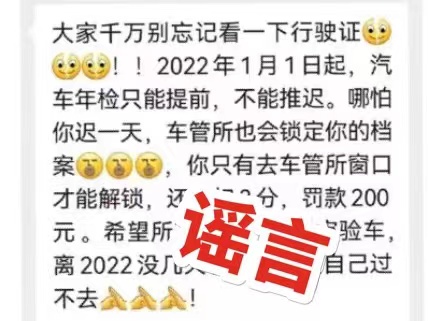人类是习惯的奴隶。学者这样想。
即使是刚降临到世界上的婴儿,早在娘胎里时,就已经养成了偶尔运动的习惯。不同地区的孕妇在孕期内饮食不同,也会影响到新生儿的饮食习惯。
地球人如此,火星人也一样。
 (相关资料图)
(相关资料图)
有些人万千次练拳、挥剑,目的就是将多余的动作从习惯中去掉。他们这样做,无非是从一片污水中迈进另一池清澈些的水里。
不过在学者眼中,只要仍站在水中,挂在这些人身上的水珠,就足以沉重得让他们迈不开步子。
支起身子,身上的伤口太多,血液洇满他破碎的的衣服。遍身的痛让他似能听到全身伤口都在制止他继续行动。
一步迈出,学者看到阿祁纳对着空荡荡的墙角轰出一拳。
他已经没有力气说更多的话,也不再有话想对阿祁纳说。
他只想杀死这个选择入局却对地球一无所知的火星人。
看着眼前高大的背影,学者运作空气中的魔力,在指尖上烧起一束火苗。
“如果你的第二步就是阻止我……”
学者在心里默默念着,话到一半,忽然不愿意再读给自己听。
“我一定不会让你走上这条,我亲自领你来的路。”
告别的话对自己也藏了半句,学者将指尖火焰缓缓向植物盔甲上送去。
“呼!”
腥风再度吹起,沉实的拳迅雷般砸在学者头上。身体飞出去的前一刻,学者看到阿祁纳眼中的雾散了。
“到最后,你依然只顾着改造我的习惯。
“组成这身盔甲的可是火星植物。别忘了,植物也有植物的生存本能。”
拖着学者的身体,阿祁纳慢慢走回赵伯的旅馆。来到巷口时,她远远看见旅馆前站着两道身影。一人是穿着灰布袍,打扮低调的上官宛凝。另一人则看着眼生,穿着一身相对干净的白衣,二人似乎正在交谈着。
听到身体在地上拖行的声音,那人向巷口扭过头。随后上官宛凝也看过来,见到阿祁纳走过来,便迎上去。又看到阿祁纳手里提着学者洇血的身体,原地踌躇了下,指着问道:“你把他怎么了?”
“再不收拾掉,城里的人们就都要被他影响了。”阿祁纳想把学者的尸体提到旅馆门口。想想又觉得不对,于是一松,放任他上半截身子掉在地上,“到时候就来不及咯。”
她转问起身边的白衣青年“这位兄弟是?”
上官宛凝看着阿祁纳,忽然愣了一下,又连忙介绍起,“这位是秋灵,是天使,也是名医生。”
穿着白衣服的青年却轻轻摇头:“现在不是了,请别再那么叫我。如今我会经过这里,仅是以天使的身份。”
他语气平静温柔,却引得阿祁纳不禁思考起来:世间确有其天使族的传说,不过传言中的天使族独立于这片宇宙之外,又为什么会出现在地球?
“先不说这些了,我刚才已经用神术让团团的伤势稳定下来,我们进去看看吧。”秋灵却将话点到为止,推开旅馆大门,先走了进去。
壁炉里的烈焰仍不见颓势,明亮的火光照出围坐在餐桌旁四人的影子。阿祁纳数了数,张团团、可米、玉剑、赵伯。只有张团团斜靠在一张皮包椅背的椅子上,衣服下露出的手臂上打着绷带,看起来虚弱,却也和其他人一样集中注意,看着推门进屋的三人。
“团团,你怎么样了?”阿祁纳走近张团团,后者轻叹出一声“还好”就不再言语。
“趁我不注意先回来了是吧。”她又看了看可米和身边的上官宛凝,勾起嘴角,拉来张椅子也坐在餐桌边,“小姐妹们打算留我一个人对付学者?”
才说完这句话,她就注意到坐在桌另一侧的赵伯胳膊颤了下。她下意识地抿了抿嘴,忽然听见可米的声音:“没事,赵伯也是我们反抗团的一员。他知道学者的事,不用隐瞒。”
说完,她又对阿祁纳问:“听宛凝说,我给她的那颗种药被送到了你这里?”
阿祁纳点头:“你叫它…种药?那里面存储着种子的生命力,这个名字倒很贴切。不过,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具体原理我也不理解,不过,这可是反抗团的大家智慧的结晶。”可米看向赵伯,又将目光依次扫过张团团、上官宛凝和阿祁纳,“它原本作为药品从南方的人们手中运输过来,前天我们送出镇的那车货物也都是这类种药。”
阿祁纳点点头:“这么说,那些在货站接应货物的人,也都来自你们的反抗团?”
“是的,魔王推翻王国的统治之后,虽然不派人烧杀抢掠,但是也在不断阻止新势力诞生。所以很多城市都如孤岛一样,出现了自己的地头蛇,欺压百姓,做着魔王军没做的事。”
“然而没有城市能变成一座真正的孤岛。盛产松脂,依山建立的松雪城需要大量粮食维持生命。位于西边的柳瑙镇需要木柴和圣石烧火度过严冬。南方的月溪城则缺少大量的石材建筑新城区。于是城中经历苦难的人们有了交流的机会,没过多久,反抗团——这个存在于桥梁上的组织就诞生了。”
“这么说来,你们的消息应该很灵通才对。之前就没怀疑过学者的身份和举措吗?”趁可米说话时,阿祁纳与上官宛凝对了个眼色,随后问道。
“别把我们想得太厉害,他是魔王军,在他面前我们也只是手无寸铁的普通人。就算看穿他的身份,冒然行动也会牵连更多人。”赵伯叹出一道绵长平缓的气,又说,“他在这里生活几日之后,就摸清了我们的一部分习惯……”
“连我也没想过,那时就上了他的套。”餐桌对侧,玉剑披着大衣,似乎有些消沉,“凶手居然可以利用超能力犯罪,这从一开始就对侦探很不公平嘛。不过我怎么都想不通,他费尽心思观察我们的生活,用魔王的能力影响我们,究竟是为什么?”
阿祁纳回想起学者生前絮叨的样子,只觉得没什么不可说的话:“他想改造……”
改造,他想改造谁?
话到嘴边,措辞却换了一种。
“他想改造‘大家’。简而言之,他认为改造习惯能让我们的世界更美好,就像创造了一个乌托邦。”
“乌托邦?”可米明显对这个陌生的名词不理解,赵伯也露出有些迷惑的表情,他看向桌脚。
玉剑却恍然大悟一般点点头:“乌托邦,乌托邦……可他的乌托邦里却出现了王剑,这就是他创造的乌托邦里,存在的不完美之处吗?”
“是啊。他的幻想,出发点很好,却不正义,也不尽善。”阿祁纳如此应道。
“但是他没机会看到这处不完美了。”上官宛凝遗憾地摊开手,“不过他祸害了这么多人,又伤了团团。作恶多端,也不值得可惜。”她又看向秋灵:“如果不是这位好心人路过这里,恐怕我们现在还很难控制团团身上的伤势。”
众人视线聚集在白衣男子身上,他似乎毫不意外于自己忽然成为谈话的焦点:“对付魔王,我们从来都在同一立场。”
声音平淡温润,令人倍感亲切。
“我相信这次相会是善良的巧合。”秋灵也将目光投向上官宛凝,“那么,为了防止下次再出现类似的情况。各位还是先去大城镇的医院里,多买一些伤药再行动才安全。”
可米盯着神态淡然的秋灵,心中泛起一股说不清的古怪感。她对这人的来处很好奇,照理说这个时间进村,无论如何都会和安比托卡大森林扯上关系。如果他打算南下走进森林,却什么行李都不带,他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他是赶夜路从森林走出,来到小镇,又为什么不见疲态,素净白衣一尘不染?
刚才他救治张团团时,紧闭起房门,过一会儿就出来了。如果真要将每处伤口都用药消毒,再逐个打上绷带,那么短的时间内可能完成么?
想到这里,她忽然听见上官宛凝语气沉重道:“可惜,我们的路费都在这里被偷走了。那个小贼偷钱到手,又被这附近一伙骑马的强盗劫去。”话末,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
“那真是,太可惜了。”秋灵微沉下头,目光同情:“我身上也没带太多钱,不过足够帮各位冒险者付上在这里住段时间的费用。团团之前伤势严重,最好还是等她把伤养好再出发。”
“别这样,秋灵先生。你刚刚救了我,我感谢你还来不及,怎么好意思花你的钱呢。”
从阿祁纳进门时便保持沉默的张团团忽然开口:“而且我感觉我体质还不错,恢复得应该很快。”
“体质好,那就好呀……”
秋灵轻点着头,正要说什么时,屋外忽然传来一阵杂乱的马蹄声。他辨认着,似乎是从远处的大街上传来的。
其他人显然也听见这古怪的马蹄声,阿祁纳问:“这是外面那伙强盗闯进镇里了?”
赵伯说:“镇里哪家的马车都折腾不出这么大动静,我去看看。”说着,便起身向屋外走去。
一旁的秋灵和上官宛凝见状,也跟着走出屋外。张团团慢慢支起身子跟上大部队。可米原本想拦,却犹豫了会儿,最终跟在她身边一起走过旅馆外的窄路。来到巷口,竟看见大街上丢着许多支深色布袋。有些袋子绑绳散开,阔口倒在地上,露出其中成堆的钱币。
上官宛凝和秋灵是最先赶到巷口的,他们来时,马蹄声已渐微,只看得见一队骑马的身影向镇外圣城的方向行远。
“你们的钱回来了?”秋灵有些疑惑地问。
上官宛凝不作声,只是远远凝视着那队身影消失的方向。
“事不过三,我最后劝你们一次,别去。”
阿祁纳站在小巷中,看着自己的右手。一滴水珠从她的食指上滑落,不知为何,她觉得这是一滴沉重的雾。
“行啦,你就以这样的形象留在别人心里不是挺好吗?一个向往乌托邦,却手段偏激的失败者。”她抹开这滴不知从哪处落在手上的水,“别不甘心了,我从来没有义务成为你写给这段历史的遗书。”
你的理念啊,你的梦想啊。应该和你的死亡一样独属于你。